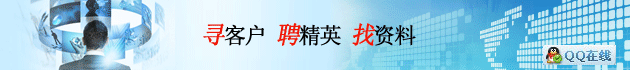一把一次性活的檢鉗168.3元,它究竟長的什么樣子?王女士想一看究竟,不過,醫生以成為醫療垃圾為由拒絕了王女士的要求。
據記者了解,一次性活檢鉗屬于醫用耗材,是醫療器械的一部分,與CT、B超、核磁共振等所用的設備相比,耗材是消耗品,每天都在消耗,需要長期投入。
“活檢鉗分為一次性活檢鉗和可復用的熱活檢鉗,一次性活檢鉗應是在征得患者的同意的情況下使用,畢竟,很多一次性的醫用耗材并未納入醫保,相比復用耗材費用也較高。
但是,近年來,醫改的關注重點大都在破除‘以藥養醫’上面,那么,醫藥不加價了,部分醫院便將利潤點轉移向了醫用耗材上,從而增加了醫用耗材的使用,用來擴大醫療收入這個‘分母’,以至于醫用耗材過量使用成為‘潛規則’。”一接近醫療結構的業內人士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次性活檢鉗屬于普通的醫用耗材,心臟起搏器、支架、骨板這些價格動輒成千上萬的高值耗材的濫用以及過度檢查更應是醫療監管的重點。
曾有數據表明,在衛生材料中,高值耗材占比通常達到百分之五六十,有的甚至高達80%。
耗材占比一度高達80%
醫改最早從2006年就確定政府主導,建機制,要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衛生制度,要讓醫療衛生回歸公益性,這個理念當時是超前的。但具體實施起來步履維艱。
記者通過整理數據發現,2006年,我國衛生總費用為9843.34億元其中,政府衛生支出1778.86億元,個人衛生支出4853.56億元。而這一數據到了2017年,我國衛生總費用51598.8億元,其中,政府衛生支出15517.3億元,個人衛生支出14874.8億元,2018年的衛生總費用支出更是接近了6萬億元。
十幾年間,政府真的是加大了資金投入,我國衛生總費用也增長了6倍,個人衛生支出的占比也是逐年下降,但是,老百姓的獲得感依然不強,看病難、看病貴依然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其中,藥品銷售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偏高直接形成了我國“看病難,看病貴”的頑疾。
據記者了解,“以藥養醫”一直是醫院籌資模式的主要渠道之一,藥費占比往往能達到醫院收入的40%-70%,北京、上海等地區醫院的藥費占比甚至更高。
直到2017年9月底,全國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自此,在我國實行60多年的藥品加成政策退出歷史舞臺。隨之,提高財政補貼、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成為彌補醫院政策性損失的兩個主要渠道。隨著我國醫改各項政策的深入推進,針對藥品,從公立醫院集中采購到流通“兩票制”,再到終端零差率、藥占比嚴控、規范合理用藥等舉措切實落地,藥品費用高增長得到明顯遏制。
然而,在諸多公立醫院藥占比下行的趨勢下,卻伴隨著各類檢查性項目的量價齊升,致使醫療服務費用增長較快,百元醫療服務收入中耗材占比居高不下,而這顯然違背了醫改的初衷。
“我們只是單方面的破除了以藥養醫,并沒有改變我國公立醫院要自負盈虧的體制機制,加之政府對醫院的財政投入越來越低,為此,在降低藥占比及全國推行藥品零加成政策后,醫院損失的部分需要從其它途徑補回來,其中,提升耗占比便是一項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措施。”上述人士表示,破除了藥材養醫后,不少醫院陷入了通過過度檢查、提高耗材占比養醫的格局,在衛生材料中,高值耗材占比通常達到百分之五六十,有的甚至高達80%。
曾有媒體報道,一枚出廠價不到三千元的支架,到了患者身上就要賣到一萬塊錢左右,有些進口的支架,甚至可以賣到兩萬多。從廠家到患者,價格翻了三倍到十倍。
除了支架,還有更夸張的。南京就曾出現過天價螺絲釘,一枚骨科手術中使用的醫用螺絲釘,市場價只有六十多塊錢,但是廠家的報價竟然高達一千五百多塊,是市場價的二十多倍。
醫療耗材價格不能“一控了之”
在藥品零加成全面實施后,醫療器械的定價亂象開始凸顯,醫用耗材成為了下一個重點監控的對象。
2017年7月,九部委聯合發文,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專項針對醫用耗材的聯合整治行動。當時,原國家衛計委曾要求各醫療機構需要將耗占比(醫用耗材在百元醫療收入中的百分比)控制在20%,旨為醫院可以“少用貴的只用對的”。
但實際上,不同的醫院耗占比是不同的。醫院級別越高,進行的手術越復雜,使用的耗材也相對高端,耗占比一般也就更高,而較小的醫院往往承擔常見疾病的治療,更多是低值消耗。各科室的耗占比也是不一樣的。比如一般外科能達到25%左右,耳鼻喉在百分之七八,糖尿病醫院低;骨科、血管外科、脊柱科、大血管等,比例都很高。
“一刀切”的結果就是,當年年底,便有多地公立醫院被傳醫用手術耗材被限用,影響到了患者治療。
原來,公立醫院為了完成降耗任務,一方面會通過集中采購、直接向供應商砍價、縮減供應商渠道等方法來降低耗材采購價格,另一方面也會加強控制醫用耗材的使用管理,為此,為了年終考核時讓上級檢查組看到一個“漂亮的數字”,部分醫院甚至通過停用部分醫用耗材等“突擊控費”的形式控制耗占比的降費指標。
如此一來,耗占比是降下來了,也減輕了患者負擔,減少了醫保支出,不乏良好初衷,但是影響了醫療秩序,顯然不是善治之舉。
于是在2018年3月,在國家衛健委聯合5部委發布的《關于鞏固破除以藥補醫成果持續深化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通知》中明確,將控費指標細化分解到每家醫院,不搞“一刀切”。根據耗占比的計算公式,除了不同醫院不同指標,耗材價格和醫院收入結構也是耗占比的決定因素之一,這與近年來國家要求耗材集采降價和提高醫療服務收入的舉措是相呼應的。同時,定下了2018年及以后深化醫改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其中并明確提出,要逐步推行高值醫用耗材購銷“兩票制”。
醫用耗材“兩票制”是指由醫療器械生產企業到經營企業開具一次發票,經營企業到醫療機構開具一次發票。
除此之外,福建、安徽、天津、北京、山東、寧夏、貴州、湖北、廣東、江西、江蘇、廣西、湖南、遼寧、四川、新疆等近20個省(直轄市)宣布取消醫用耗材加成。其中,福建、天津、廣東、四川、新疆、遼寧已全面啟動取消醫用耗材加成,安徽、山東、湖北、江西也有部分地區及醫院開始實施取消醫用耗材加成,北京將于2019年6月中旬起實施此改革。
“事實上,醫療耗材濫用,價格高是治理的重點,但并不是說所有價格高的都可以視為不合理而一刀切,畢竟醫療耗材的選用,與醫療技術與服務密切相關。”上述人士表示,醫用耗材不能通過“控費”一控了之,這類價格的理性回歸最終還是要靠市場競爭,同時,加強對醫院醫療過程中耗材使用的日常監督。